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雷内·玛格丽特的视觉哲学解码

倪华夏
中国美术学院
引言
20 世纪中叶,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在无意识探索的维度上形成深刻共振。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员,雷内·玛格丽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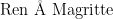 )的作品始终游走在图像与语言、可见与不可见的交界处,以看似荒诞的视觉悖论叩击着人类认知的边界。这位自视为 “用图像思考的哲学家” 的艺术家,通过烟斗、苹果、遮蔽的面孔等标志性符号,构建了一个充满语言学隐喻与精神分析张力的视觉场域。尽管尚无直接文献证明玛格丽特受拉康理论影响,但其创作逻辑与拉康提出的镜像阶段、凝视理论、小客体 a 等概念存在惊人的同构性 —— 两者均以 “断裂” 与 “缺失” 为切入点,揭示人类主体在符号系统中的异化状态。
)的作品始终游走在图像与语言、可见与不可见的交界处,以看似荒诞的视觉悖论叩击着人类认知的边界。这位自视为 “用图像思考的哲学家” 的艺术家,通过烟斗、苹果、遮蔽的面孔等标志性符号,构建了一个充满语言学隐喻与精神分析张力的视觉场域。尽管尚无直接文献证明玛格丽特受拉康理论影响,但其创作逻辑与拉康提出的镜像阶段、凝视理论、小客体 a 等概念存在惊人的同构性 —— 两者均以 “断裂” 与 “缺失” 为切入点,揭示人类主体在符号系统中的异化状态。
拉康理论的独特价值在于将精神分析从个体病理层面提升至哲学人类学高度,其提出的 “凝视作为他者的欲望”“真实界的不可符号化” 等命题,为解读玛格丽特作品中 “图像的抵抗性” 提供了钥匙。本文试图以拉康的三大理论维度 —— 语言的能指链、主体的他者性、视觉的分裂性 —— 为框架,解析玛格丽特如何通过绘画实践,完成对西方传统认识论的解构与重构,进而揭示超现实主义艺术作为 “视觉精神分析” 的哲学本质。
一、语言囚笼的突围:能指链的断裂与真实的显隐
在拉康的象征秩序中,语言作为能指链构成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个体通过习得语言进入社会共同体,同时也被能指的霸权所规训 — “主体的存在被语言所掩盖,滑落到符号之下”(Fink, 1997)。玛格丽特的《图像的背叛(这不是一支烟斗)》(La trahison desimages)正是对这一符号暴政的公然挑战。画面中写实的烟斗下方,画家以工整字体写下 “Cecin'est pas une pipe”(这不是一支烟斗),直接撕裂了图像与语言的传统契约。
从拉康的能指理论视角审视,这幅画作呈现了双重能指的对抗:作为视觉能指的烟斗图像与作为语言能指的 “烟斗” 文字,本应在象征秩序中形成指涉闭环,却在此处产生剧烈断裂。柏拉图曾将绘画视为 “对理念的三重模仿”,而玛格丽特则更进一步,通过符号的自我指涉性,将绘画从 “模仿论”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 画布上的烟斗既非实物的摹本,亦非语言的图解,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本体论地位的符号实体。这种对 “模仿” 的超越,暗合拉康所说的 “模仿揭示的并非原型,而是差异本身”—— 图像不再服务于 “再现真实” 的工具理性,转而成为暴露语言空洞性的认知装置。
拉康将 “真实界” 定义为 “无法被符号化的创伤性剩余”,它始终在语言之外徘徊,却又以悖论性的方式渗透进象征秩序。玛格丽特的烟斗系列作品,正是通过制造符号断裂,迫使观者直面语言无法捕捉的真实界。当观众被 “这不是一支烟斗” 的文字拽出 “图像即再现” 的惯性认知时,他们被迫面对一个根本困境:语言标签永远无法穷尽事物的存在,真实始终以“剩余” 的姿态逃逸于符号网络之外。
这种对语言局限性的揭示,在《文字的使用》(L’usage de la parole)等作品中达到极致。画面中,日常物品被密密麻麻的文字覆盖,苹果、瓶子等实体与标注它们的词语激烈碰撞,形成视觉与语义的短路。拉康认为,“无意识的结构像语言一样被建构”,但玛格丽特却通过图像与文字的对抗性并置,暗示无意识领域恰恰是语言秩序的 “飞地”—— 那里蛰伏着无法被能指链捕获的原初欲望,如同真实界的幽灵,在符号的裂缝中闪烁。
在传统认识论中,“命名” 是人类掌控世界的基本方式 —— 亚当为万物命名的神话,隐喻着语言对存在的征服(Harkness, 2003)。但玛格丽特的创作却始终在进行 “去命名” 的解构工作:《集体发明》(L’Invention collective)中,机械零件与生物器官诡异地融合,拒绝被归入任何既定的语义范畴;《人类的处境》(La Condition humaine)里,画中画的结构制造了现实与再现的无限递归,消解了 “真实” 的终极所指。
这种对命名权的反抗,本质上是对拉康所说的 “大他者” 权威的挑战。在象征秩序中,大他者通过语言系统赋予事物意义,而玛格丽特的图像则如同刺入能指链的尖刺,制造意义的短路与延异。正如福柯所言,玛格丽特的作品揭示了 “词与物之间漂浮的、不相称的关系”(Foucault, 1973),这种关系不是对现实的扭曲,而是对语言中心主义的颠覆 —— 当图像不再臣服于文字的统治,真实才得以以其破碎却鲜活的姿态悄然显形。
二、他者凝视的剧场:主体建构的视觉政治
拉康的 “镜像阶段” 理论揭示了主体形成的根本性悖论:婴儿通过认同镜像中的理想自我完成自我建构,却从此陷入 “以他者为中介的异化”。这种异化在视觉艺术领域的表现,即是观看与被观看的权力结构。玛格丽特的《尝试不可能的事》(L’Essai du impossible)直击这一悖论 —— 画面中,男性画家俯身凝视着裸体女模特,画笔在画布上复刻着她的身形,而模特的目光则空洞地望向画面外,仿佛沦为画家凝视的傀儡。
这幅作品构建了三重凝视关系:画家对模特的物理凝视、画布对模特的符号凝视、观众对画作的元凝视。拉康认为,“凝视不在主体这边,而在客体那边”(Evans, 1997),在此情境中,模特作为被凝视的客体,其主体地位被画家的凝视彻底消解 —— 她的存在仅仅作为画家欲望的能指而存在,如同镜像阶段中的婴儿,通过他者的目光获得虚幻的自我统一性。这种对“观看即权力” 的批判,预演了后来女性主义理论对男性凝视的解构,而玛格丽特则以超现实的构图,提前揭示了视觉政治的暴力本质。
在拉康的理论中,“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主体的欲望永远指向他者所欲望之物。这一命题在玛格丽特的自画像系列中呈现出复杂的张力。《戴黑帽的自画像》(Autoportrait auchapeau noir)里,画家将自己的脸隐藏在巨大的黑帽阴影中,只露出一双凝视观众的眼睛。这种自我遮蔽打破了传统自画像的 “自我呈现” 逻辑,暗示艺术家的创作欲望本质上是对 “他者目光” 的回应 —— 画家渴望被观看,却又恐惧被彻底看透,于是在暴露与隐藏之间制造永恒的延宕。
观众在面对这类作品时,同样陷入欲望的陷阱:我们试图通过画家的眼睛捕捉其真实自我,却发现自己始终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凝视结构 —— 正如拉康所说,“当你看着画时,画也在看着你”。玛格丽特通过这种凝视的倒置,将观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主动的被凝视者,迫使我们直面 “观看” 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权力的实施,而主体永远在他者的目光中沦为欲望的客体。
超现实主义对身体的呈现始终充满叛逆性,玛格丽特的《强奸》(Le Viol)即是典型案例。画面中,女性的面部被身体的其他器官覆盖,传统的 “面孔 - 身份” 关联被暴力拆解。从拉康的 “想象界” 理论来看,面孔是自我认同的核心能指,是 “我” 与他者建立想象性契约的媒介。而玛格丽特的解构,实则是对 “身体作为意识形态战场” 的揭示 —— 当面孔不再作为个体性的标志,身体便回归为纯粹的物质存在,暴露出其被文化符码层层包裹的真相。
这种对身体能指的肢解,呼应了拉康关于 “部分客体” 的论述。在《主体的构成》中拉康指出,婴儿最初感知的身体是 “碎片化的、非整合的”,而镜像阶段的认同正是对这种破碎性的想象性修复。玛格丽特的作品则逆向而行,通过呈现身体的非整体性,打破 “完整自我” 的幻象,揭示主体本质上是 “他者欲望缝合的产物”。《强奸》中的身体不是情色的对象,而是一个充满创伤的场域,那里凝结着社会规训与个体反抗的永恒博弈。
三、可见性的辩证法:遮蔽作为认知的通道
西方传统绘画的透视法,本质上是笛卡尔式主体观的视觉化表达 —— 画家以 “我思” 为中心,构建一个可被理性丈量的几何化空间。玛格丽特的《恋人》(Les Amoureux)却以激进的遮蔽手法挑战这一霸权:画面中,情侣的面孔被布料严严实实地包裹,传统透视法赖以建立的 “视觉中心” 被彻底消解。这种构图迫使观众放弃 “全知观看” 的幻想,承认自己的视角始终是有限的、被阻挠的。
拉康将凝视与眼睛的分裂视为主体性的根本特征:“眼睛是主体的器官,而凝视属于客体的场域”(吴琼,2022)。在《恋人》中,被遮蔽的面孔成为凝视的化身 —— 它们虽然不可见,却始终在场,以缺席的方式统治着整个视觉场域。这种 “不可见的可见性”,暗合了拉康对 “小客体 a” 的定义:它是欲望的成因,是 “在视觉领域中永远逃逸的剩余”。
玛格丽特对 “面孔遮蔽” 的执着,被学界普遍关联到其童年创伤 ——1912 年母亲投河自尽,尸体被打捞时面部被睡衣覆盖的场景,成为艺术家挥之不去的心理印记。从拉康的 “真实界” 理论出发,这一创伤事件作为 “未被符号化的实在”,始终以不可言说的形态蛰伏于主体无意识中。《恋人》中笼罩面孔的织物,与其说是对亲密关系的隐喻,不如说是创伤记忆的视觉转译 —— 那些无法被语言表述的痛苦,只能通过 “遮蔽” 这一悖论性符号得以呈现。
拉康认为,“真实界以创伤的形式返回”,而艺术创作正是将真实界转化为象征秩序的中介。在《无题(人脸与鸽子)》中,鸽子扑扇的翅膀遮蔽了半张人脸,羽毛的轻盈与表情的凝滞形成张力。这种遮蔽并非简单的视觉游戏,而是创伤的 “延缓性运作”(Nachträglichkeit)—— 如同弗洛伊德描述的延迟性创伤,玛格丽特通过反复的图像编码,试图在象征界中为不可言说的真实界找到栖身之所。遮蔽在此成为一种创伤的 “治愈性暴力”,通过可见之物的缺席,迫使观者直面不可见的心理深渊。
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小客体 a”(objet petit a)是欲望的成因,它既非具体客体,亦非纯粹虚无,而是 “象征秩序中的空隙”。玛格丽特的《人之子》(Le Fils de l’homme)堪称这一概念的完美图示:画面中,戴礼帽的男子面前悬浮着一颗硕大的青苹果,恰好遮挡住他的面孔。苹果作为典型的 “部分客体”,在此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视觉上的障碍物,阻断了观者与人物的眼神交流;又是欲望的诱饵,激发观众对 “被遮蔽之物” 的想象性补全。
这种 “遮挡 - 诱惑” 的机制,暗合拉康对小客体 a 的界定:“它是你所看到的与你所没看到的之间的落差”(Zizek, 2006)。当观众试图绕过苹果窥视人物的真实面容时,他们实则陷入了欲望的永恒循环 —— 因为被遮蔽的面孔本身就是欲望的空洞,而苹果作为小客体 a,不过是填补这一空洞的临时能指。玛格丽特通过这种视觉诡计,揭示了人类认知的根本困境:我们永远在追逐符号链中的缺失,却浑然不知那缺失正是欲望的源头。
传统视觉理论将 “看” 视为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把握,而拉康则通过 “凝视” 概念颠覆了这一认知:“凝视不是主体的功能,而是客体对主体的召唤”(Evans, 1997)。玛格丽特的《戴礼帽的男人》系列中,人物的面孔或被阴影吞噬,或被镜面反射扭曲,始终拒绝被视觉系统捕获。这种 “不可见性” 迫使观众从 “观看者” 转变为 “被观看者”—— 当我们以为在审视画作时,画中人物那不可见的凝视早已穿透表象,直抵主体的无意识核心。
这种范式转换在《虚假的镜子》(Le Faux Miroir)中达到哲学高度:画面以超写实手法描绘一只仰望天空的眼睛,虹膜中倒映着蓝天白云,却唯独缺少瞳孔的聚焦点。拉康曾以 “眼睛是一盏灯” 隐喻主体在凝视中的被动性,而这幅画作恰如其分地呈现了这种被动性眼睛不再是主动观察的器官,而是成为他者凝视的接收器,虹膜中的蓝天白云不过是象征秩序的幻象,真正的凝视来自瞳孔深处那不可见的虚无。
结论
雷内·玛格丽特的绘画实践本质上是人类认知极限的视觉实验,借拉康精神分析可揭示其三重复合哲学对话。
在语言与真实维度,其以《图像的背叛》的 “烟斗悖论” 瓦解语言能指链稳定性,通过图像与文字的对抗,揭示语言作为象征秩序核心的双重性:既是认知工具,也是异化牢笼。画作中的图像成为刺入能指链的 “真实界碎片”,在语言失效处显露出存在的偶然性与不可符号化本质。在主体与他者的视觉政治中,艺术家通过镜像结构与凝视倒置解构 “观看即权力” 逻辑。无论是《尝试不可能的事》中画家与模特的二元对立,还是自画像中观众与画作的凝视博弈,均体现拉康 “主体在他者场域异化” 的命题 —— 人类通过他者目光建构自我,却永远无法触及真实主体性,观看本质为权力对主体的规训。在可见与不可见的辩证关系中,玛格丽特以遮蔽、错位构图挑战西方视觉中心主义。《恋人》中遮蔽的面孔、《人之子》中悬浮的苹果,打破透视法全知视角,证明认知突破存在于视觉逻辑断裂处 —— 即拉康 “小客体 a” 的领域,那里是欲望成因与真实界创伤的交汇点。
从思想史看,其创作与拉康理论共同批判现代性认识论,揭示启蒙理性下语言与视觉秩序的局限性。玛格丽特以 “不可见现实” 的追寻,使画作超越视觉奇观,成为叩击认知边界的哲学寓言。在图像过剩的当代,其启示我们:真理栖身于语言与图像的断裂处,需以凝视的勇气在 “不可见” 中抵达认知本质。
参考文献
[1]Atwood, M. (1997). Alias Grace. New York: Anchor Books.
[2]Diatkine, G. (2007). Lac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8, 643-660.
[3]Evans, D. (1997).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4]Fink, B. (1997). 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吴琼. (2022). 《拉康式观看:眼睛与凝视的分裂》. 西南大学出版社.
[6] 高荣禧. (2007). 《西方艺术中的女体呈现- 福柯的启迪》. 台北:唐山出版社.
[7] 王国芳,郭本禹. (2003). 《拉康》. 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 拉康 . (2001).《拉康选集》. 上海:三联书店 .
.jpg)
.jpg)
.jpg)
.jpg)
.jpg)
.jpg)